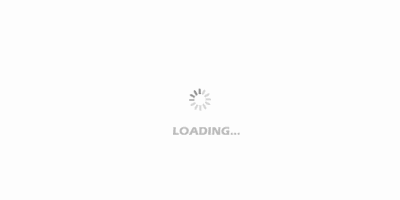盤絲洞裡,所有的道具都被堆在了一邊,那口棺材已經不見。人去樓空般的不留痕跡。
聞不到死亡的氣息,甚至連冰冷的感覺也沒有。
難道我的懷疑是錯的嗎?
明在那堆雜木裡翻找了半天,依然毫無收穫。他轉過身來,聳聳肩。我四處走動,沒有任何足以讓人懷疑的東西。
“出去看看!”明這樣提議。
就在我們踏出洞口的一瞬間,我滿心期待又害怕出現的事情終於發生。燈突然的滅了。
我沒有絲毫的詫異,他還是會來的。
冰冷又慢慢升了上來。
明打開了手電筒,我們站立不動。
在手點筒的燈光一晃照到的地方,
我拉著明,向洞裡走去。
洞的中央擺著一張大床,有帷幕的大床,看不清顏色,只是它黑壓壓的遮掩著床,床上有個做女裝 打扮的木偶,她躺在那裡,在她的身上壓著一個臉朝向她脖子的人。是吸血鬼,他披著黑色的風衣 ,看不見身體。
大概她是快樂的吧,她臉上浮現出一絲笑容,那是種受蠱惑的快樂吧。
腳步聲消失了。明走到一邊四處摸索,而我則來到了床前。
站在這個謀殺者和被謀殺者的身邊,我緊緊握住了拳頭。我知道他們也可能是被操縱的利器,再次充當謀殺者的角色。
我的眼睛注意到了披風的一角,它被沉甸甸的拽下,像是有什麼東西在口袋裡。我正向它伸手。
聽見明在叫我,“清樹,快過來!”
我走到了他的那邊,順著他指的方向向下看。地上有一灘粉末似的東西,它看上去沒有石灰那麼凝重,但也不是粉筆灰塵那麼輕盈。明小心的蘸了一點,放在鼻子下聞了聞。
他搖搖頭,它沒有味道的。
太過於專注這片粉末了,而忘了身邊的變化。
待我回頭來,吸血鬼已經不見了。
手電筒的光圈裡沒有吸血鬼,那個女裝 打扮的木偶兀自躺在那裡。
“清樹!”明呼喚我。
陰冷的感覺再次俘獲了我的心,我知道他就在附近。
我四處的回頭,像是身後就有冰冷的呼吸。
將手電筒照向了明,在他的身邊是飄揚垂下的披風,
明絲毫沒有察覺出危險,他關切的看著我。
在我還沒有喊出聲前,吸血鬼張開雙臂緊緊的摟住了明。喊叫聲被我硬生生的吞了回去,耳邊即刻傳來明的吼聲和他的喘息聲。
“放開我!”
我向前邁了一步,焦急灼燒著我的心,我恨不得一步沖上前去,救回明。可是馬上我呆立不動。
因為我看到了吸血鬼身後的人,那個操縱木偶的人,那個擁有死神目光的人,他隱在了黑暗裡,或者說他和黑暗本就是一體。
他的眼睛發出冰冷的寒光和殺機。像躲在白卓身後一樣,他在邪惡的藐視另一個生命。
他在我的眼前殺害了我們,比殺死我更讓人難以忍受。
我聲嘶力竭的叫喊了一聲,即刻聲音在洞裡四處的徘徊。我也不知道是因為我無力,還是因為怨恨。
心裡一陣錐心的痛。燈豁的亮了。
耳邊一陣風過,一個身影從我的身邊晃了過去,他即可伏到了明的身前,和明的身體重疊。
那是熟悉的背影。
心裡響起了一個聲音,是白卓,他居然是白卓。
他再次的出現,居然是白卓。
心裡百味交集。當我回過神來的時候,他已經拉著明走到一邊,明臉色蒼白,兀自喘息,而白卓還是那副樣子,乾淨的頭髮,白淨的臉,只是沒有任何的血色,連嘴唇也是白色的。
當一個從你生活裡消失了很久的東西或者人再次出現的時候,除了驚喜,你會不會有一點擔心,擔心這樣的日子馬上逝去。
我馬上走到了他們的身邊,
我知道他並沒有呼吸。
明也沒有說話,我們的敵人潛伏了起來。只有吸血鬼倒在了一邊。
洞裡沒有任何的聲息。
我和明站在了白卓的兩邊,摒住了呼吸。
當冰冷襲上來的時候,心裡卻意外的平靜。這是我第一次面對他時,能夠保持平靜。是因為白卓站在身邊,還是剛剛的一口悶氣得到了釋放,還是這個故事終於要面臨結尾了。
我的直覺告訴我這個故事就快要完結,結果不外乎兩種,要麼是他死,要麼是我們死。
他爬了出來,是的,他從地上向我們爬了過來。
他垂著頭,黑色的衣服,笨拙而寬的身體。我想起在行政樓的會議室裡那個向我爬過來的人。
他的頭髮也慢慢變長,
他一點點向我們逼近,他慢慢的仰起臉,他的臉上也滿是濃密的頭髮。
在離我們一米遠的時候,我看看身後,是那張床。
我拽緊了拳頭,腳在暗暗加勁。
我知道我要做什麼了。
同樣是必死的決心。
他猛的向前一撲,他的目標顯然是明。
黑色的頭髮在我眼前一晃,頓時熱血湧上了頭頂,讓一切都完結吧。
我向他撲了過去。
只是,只是白卓搶先了一步。他已經抱住了他,我看見白卓的臉已經扭曲,我知道他已經使出了全身的力氣。
他和他糾纏在一起,倒在了那張床上。他的手插進了他的頭髮裡,他的手插進了他的背裡。
沒有血,只有皮肉嘶開的聲音。
和骨頭碰撞的聲音。
這一幕我將永遠的記在心裡。白卓朝著我們喊:“快點火!”他的聲音在發抖,他還是感覺得到痛苦嗎?
明慌慌張張的掏出打火機,我第一次看見明抖得這麼厲害。
其實不是害怕,而是因為眼前的一人是我們的朋友。
火跳躍了起來。
明猛的向前一擲,碰,一聲巨響。火苗竄了上來,燒到了帷幕。
馬上床上的兩個人陷入了火海。
看不清他們的表情。
只剩下木然的我和明。
在吸血鬼的口袋裡發現了那後本部分的日記本。
願一切得到安息。
借著火光,我看清楚了日記本前面的幾個字。“除了你,這個世界上只有你在乎我。”
夏元說的是他嗎?和白卓一齊陷入火海裡的他嗎?
我看見明呆呆的看著我,“怎麼了?”他低下頭,我看看了日記本。像是被誰打了一拳。
我也怔住了,因為我看見了他的名字。
“楊黎清木”
他為什麼會叫“楊黎”。
一段燒焦的身體捲縮地陳放在太平間,黑乎乎的樣子像是一段枯木。和這平靜的白色房間形成巨大的反差,他看不清鼻子和眼,他看不清手和腿了。
我並不害怕。
這是我第三次來到了太平間裡,第一次是風,第二次是老大,這次是白卓。員警已經證實了他的身份,只是他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經過化驗證明他已經死了很久,為什麼屍體直到現在才出現。
其實他們不明白的事情還有很多。世界上的事情又有幾人能夠看得透呢?關於生死。我一直沒有流眼淚,眼前盤旋著白卓平靜而慘白的臉,和他那句“快點火”。心裡像是被某種硬物堵著,心也是冰冷的。
我看見明一轉身,淚水便止不住的佈滿了他的臉。他象個做了錯事的孩子一樣哭得那麼無助,雙手遮臉,肩膀一個勁的抽搐。他是為點火的事情而內疚嗎?這不是他的錯,他結束了白卓的一場煎熬。
上不了天堂,也下不了地獄的煎熬。他在等著這一天的到來嗎?用自己的身體擋住了一場災難。
我的朋友,你現在在天空中微笑嗎?和風他們一起的吧!
年關逼近了,空氣中也彌漫著爆竹和溫馨的味道。小飛養了很多貓,愛心氾濫。大的,小的,黑的,白的,各式各樣。寢室裡現在是貓行霸道,不過沒有人會抗議,因為它們這些小小而柔軟的生命曾經許多次的救過我們,連管理員都沒有意見,因為這些小貓都擁有像小飛一樣溫柔的眼神了。
宏翼、志強曾經有幾天不理我和明,因為怪我們私自行動,而不帶上他們。他們為此鬧了好一陣子,無論我和明怎麼說好話,也不肯原諒我們。直到一次酒後,宏翼哭著說:“現在風,老大,白卓都不在了,如果你們再出問題,那206……”他伏在桌上,看不見他的表情,聲音被哽咽聲打斷。直到我們都紅了眼眶。
為了一段兄弟情。
冬日裡清冷而暗淡的天,17棟還是悄然的矗立在樹影裡,似乎什麼也沒有發生般的寂靜。樹影婆娑。
時間靜靜流過,不漏痕跡。像一段規定了時間的糟糕夢境。
那天我還是帶著許麗去了操場下的階梯邊,苦苦的尋覓後最終在單架下的濕土裡發現了一把小刀。刀鋒上還有一絲絲烏黑的血跡。
抬頭看到許麗的雙眸在冬日裡閃亮得如同北極星,不由感覺幸福。
一切像是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一樣,打斷了的時間和場景又重新開始了排列組合被開啟另一種詮釋。
那天兩個死去的靈魂帶我們來這裡,除了發現斧頭、麻繩和兩張紙片外,還有這把小刀。這也正是他們帶我和許麗來這裡的意義。
夏元殺死了同寢室的6個人,但是管理員不是他殺的。在我第一次看關於夏元殺人報導的時候,就被這句話所吸引。報紙上說:“17棟的管理員也被利器刺傷心臟而死。”並未肯定管理員是夏元所殺,況且在我夢境裡閃爍的一直是斧頭和麻繩,而被“利器刺傷”決非斧頭所能為。
我的夢裡還有一個人在夏元上樓時被推了一個趔趄,他大概就是管理員吧,他被另一個人所殺。
那個人就是楊黎清木。
夏元後半部分的日記裡,在9月15日這樣寫道:“其實我也不想活,我活著也沒有什麼意義。在我死之前,我一定要幹掉那些罵我是豬的人,他們6個都是豬,被殺的豬。”
在9月17日他寫道:“我很高興有你這個朋友,你為我安排得這麼好,我知道你會幫助我的,在我身後幫助我除掉障礙,我只有你可以相信了。在這個世界上,我只相信你。”
在9月20日他日記最後一段是:“只有你看得起我,還為我和他們打架。其實我也不想活的,我把我的生命交給你了。”
清木像個軍師,他才是這場謀殺的幕後操縱者。他除掉了管理員,所以管理員身上的不是斧頭砍傷,而是刀傷。另外他也殺了夏元,用鈍物擊中了他的頭部,結局了他的生命。
夏元死時應該是快樂的吧,他得到了真正的解脫。
當迷霧開始散去的時候,真相便如冰山一角,待它慢慢融化,就和水平線一樣齊了。一切變得不再重要了。
當我在防空洞裡看見夏元的皮鞋 時,感覺異樣的平靜,那個時候我就知道它不是殺人的皮鞋。它在我的夢境裡閃現,但是並不在現實生活裡閃現。
它不是出現在櫃子後的皮鞋,也不是在風家裡的皮鞋,它出現在和白卓一起燃燒的那個人身上。當大火滅了,它在醒目的出現,黑色不動聲色,烏黑油亮。
它的主人才是殺害管理員,風,老大和白卓的兇手。是楊黎清木,這場殺戮的製造者。同樣為了一段兄弟情,他開始了一場又一場的殺戮,按照他固執的理解和預想。
他引火自焚,燒了自己,但是沒有燒掉自己那顆充滿戾氣的心。
幸,還是不幸,又有人能夠理解呢?
在警察局裡,他的骨灰被一個中年人捧走的時候,那個被悲哀壓彎了腰的中年人讓我覺得有幾分面熟,似乎在記憶裡的某個角落裡有他的身影。同樣寬闊的額頭,同樣小而堅毅的眼睛,他是他的父親吧!
他粗糙的大手緊握著裝有骨灰的木盒,眼神木然。他走都走不穩。
我悲哀的看著這個父親,想起我的父親,他在我六歲時就離開了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過年了,快要離開學校了,站在天臺上。雲過風輕。
眼前的一片樹林在風裡象聖潔的唱詩班。
美妙的合音。
尾聲
4年後,我的母親帶了一個男人來我的公司。寬闊的額頭,小而堅毅的眼睛,她告訴我這是我的父親。
那個時候的他還很年輕,愛上了一個女人,並和她生了一個孩子。2年後他背棄了她,娶了另一個女人,又生了一個孩子。在這個孩子六歲的時候,他回到了第一個女人身邊。
這簡直是一個傳奇,或者肥皂劇的劇情。然而這一切是如此的逼真,連他臉上的皺紋都加重了真實性。
第一個女人是清木的母親,第二個女人是我的母親。
兩個不幸的家庭。但是她不怪他,甚至在他描述時,充滿哀怨和憐憫的看著他。
我能夠說什麼呢?我想起了那個讓我一直害怕的眼睛,還想起了在黑暗裡和他唯一一次的見面。電光火石間的相逢,卻不認識是前身的宿命。
他是我同父異母的哥哥。
也許他的眼神裡不光只是殺機吧。他的父親這樣描述他:“從小他就是個堅強,但是也很固執的孩子,他很少說話,也沒有朋友,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我很想跟他說話,但是他離開了M縣自己謀生,他從不回來,也不寫信。直到……”
M縣那個母親曾經帶我去過一次的地方,荒涼的地方,大概是為了勸回父親吧。
清木其實有回去看過他,只是他不知道而已,我們發現了去M縣的車票,這是他最後一次去看沒有給自己名分的父親吧,當時他的心情會是怎麼樣呢?
一個從小被稱為私生子的孩子,一個從小被稱為豬的孩子,迅速的產生了友誼。兩個卑微而可憐的生命是冬天裡相擁取暖的孩子,他們有的僅僅是彼此的體溫吧。
清木有一段時間在我們學校當過零時工,從他父親的嘴裡模糊的推斷出。他說:“從外面打工回來的孩子說在S大學裡看見過清木。”
原來我們兄弟生活得如此接近,卻感覺不到彼此的呼吸。大概也是那個時候他認識了夏元吧。
他和他更為接近。
也許當我沐浴著陽光在草地上看書時,他在一邊埋頭掃地。也許在我和朋友勾肩搭背的時候,他在一邊獨自的吃著鹹菜和饅頭。
這是個春日的夜晚,有淡淡的月光漂浮在空氣裡,輕舞飛揚。我眺望遠方,霓虹燈披著五彩的沙巾,睜著半睡半醒的眼睛。
不知道明、宏翼、小飛他們過得怎麼樣了。往事也像月色一樣漂浮了起來,溢滿了我的心。
我微微一笑。
大地一個轉身。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
明慌慌張張的掏出打火機,我第一次看見明抖得這麼厲害。
其實不是害怕,而是因為眼前的一人是我們的朋友。
火跳躍了起來。
明猛的向前一擲,碰,一聲巨響。火苗竄了上來,燒到了帷幕。
馬上床上的兩個人陷入了火海。
看不清他們的表情。
只剩下木然的我和明。
在吸血鬼的口袋裡發現了那後本部分的日記本。
願一切得到安息。
借著火光,我看清楚了日記本前面的幾個字。“除了你,這個世界上只有你在乎我。”
夏元說的是他嗎?和白卓一齊陷入火海裡的他嗎?
我看見明呆呆的看著我,“怎麼了?”他低下頭,我看看了日記本。像是被誰打了一拳。
我也怔住了,因為我看見了他的名字。
“楊黎清木”
他為什麼會叫“楊黎”。
一段燒焦的身體捲縮地陳放在太平間,黑乎乎的樣子像是一段枯木。和這平靜的白色房間形成巨大的反差,他看不清鼻子和眼,他看不清手和腿了。
我並不害怕。
這是我第三次來到了太平間裡,第一次是風,第二次是老大,這次是白卓。員警已經證實了他的身份,只是他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經過化驗證明他已經死了很久,為什麼屍體直到現在才出現。
其實他們不明白的事情還有很多。世界上的事情又有幾人能夠看得透呢?關於生死。我一直沒有流眼淚,眼前盤旋著白卓平靜而慘白的臉,和他那句“快點火”。心裡像是被某種硬物堵著,心也是冰冷的。
我看見明一轉身,淚水便止不住的佈滿了他的臉。他象個做了錯事的孩子一樣哭得那麼無助,雙手遮臉,肩膀一個勁的抽搐。他是為點火的事情而內疚嗎?這不是他的錯,他結束了白卓的一場煎熬。
上不了天堂,也下不了地獄的煎熬。他在等著這一天的到來嗎?用自己的身體擋住了一場災難。
我的朋友,你現在在天空中微笑嗎?和風他們一起的吧!
年關逼近了,空氣中也彌漫著爆竹和溫馨的味道。小飛養了很多貓,愛心氾濫。大的,小的,黑的,白的,各式各樣。寢室裡現在是貓行霸道,不過沒有人會抗議,因為它們這些小小而柔軟的生命曾經許多次的救過我們,連管理員都沒有意見,因為這些小貓都擁有像小飛一樣溫柔的眼神了。
宏翼、志強曾經有幾天不理我和明,因為怪我們私自行動,而不帶上他們。他們為此鬧了好一陣子,無論我和明怎麼說好話,也不肯原諒我們。直到一次酒後,宏翼哭著說:“現在風,老大,白卓都不在了,如果你們再出問題,那206……”他伏在桌上,看不見他的表情,聲音被哽咽聲打斷。直到我們都紅了眼眶。
為了一段兄弟情。
冬日裡清冷而暗淡的天,17棟還是悄然的矗立在樹影裡,似乎什麼也沒有發生般的寂靜。樹影婆娑。
時間靜靜流過,不漏痕跡。像一段規定了時間的糟糕夢境。
那天我還是帶著許麗去了操場下的階梯邊,苦苦的尋覓後最終在單架下的濕土裡發現了一把小刀。刀鋒上還有一絲絲烏黑的血跡。
抬頭看到許麗的雙眸在冬日裡閃亮得如同北極星,不由感覺幸福。
一切像是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一樣,打斷了的時間和場景又重新開始了排列組合被開啟另一種詮釋。
那天兩個死去的靈魂帶我們來這裡,除了發現斧頭、麻繩和兩張紙片外,還有這把小刀。這也正是他們帶我和許麗來這裡的意義。
夏元殺死了同寢室的6個人,但是管理員不是他殺的。在我第一次看關於夏元殺人報導的時候,就被這句話所吸引。報紙上說:“17棟的管理員也被利器刺傷心臟而死。”並未肯定管理員是夏元所殺,況且在我夢境裡閃爍的一直是斧頭和麻繩,而被“利器刺傷”決非斧頭所能為。
我的夢裡還有一個人在夏元上樓時被推了一個趔趄,他大概就是管理員吧,他被另一個人所殺。
那個人就是楊黎清木。
夏元後半部分的日記裡,在9月15日這樣寫道:“其實我也不想活,我活著也沒有什麼意義。在我死之前,我一定要幹掉那些罵我是豬的人,他們6個都是豬,被殺的豬。”
在9月17日他寫道:“我很高興有你這個朋友,你為我安排得這麼好,我知道你會幫助我的,在我身後幫助我除掉障礙,我只有你可以相信了。在這個世界上,我只相信你。”
在9月20日他日記最後一段是:“只有你看得起我,還為我和他們打架。其實我也不想活的,我把我的生命交給你了。”
清木像個軍師,他才是這場謀殺的幕後操縱者。他除掉了管理員,所以管理員身上的不是斧頭砍傷,而是刀傷。另外他也殺了夏元,用鈍物擊中了他的頭部,結局了他的生命。
夏元死時應該是快樂的吧,他得到了真正的解脫。
當迷霧開始散去的時候,真相便如冰山一角,待它慢慢融化,就和水平線一樣齊了。一切變得不再重要了。
當我在防空洞裡看見夏元的皮鞋 時,感覺異樣的平靜,那個時候我就知道它不是殺人的皮鞋。它在我的夢境裡閃現,但是並不在現實生活裡閃現。
它不是出現在櫃子後的皮鞋,也不是在風家裡的皮鞋,它出現在和白卓一起燃燒的那個人身上。當大火滅了,它在醒目的出現,黑色不動聲色,烏黑油亮。
它的主人才是殺害管理員,風,老大和白卓的兇手。是楊黎清木,這場殺戮的製造者。同樣為了一段兄弟情,他開始了一場又一場的殺戮,按照他固執的理解和預想。
他引火自焚,燒了自己,但是沒有燒掉自己那顆充滿戾氣的心。
幸,還是不幸,又有人能夠理解呢?
在警察局裡,他的骨灰被一個中年人捧走的時候,那個被悲哀壓彎了腰的中年人讓我覺得有幾分面熟,似乎在記憶裡的某個角落裡有他的身影。同樣寬闊的額頭,同樣小而堅毅的眼睛,他是他的父親吧!
他粗糙的大手緊握著裝有骨灰的木盒,眼神木然。他走都走不穩。
我悲哀的看著這個父親,想起我的父親,他在我六歲時就離開了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過年了,快要離開學校了,站在天臺上。雲過風輕。
眼前的一片樹林在風裡象聖潔的唱詩班。
美妙的合音。
尾聲
4年後,我的母親帶了一個男人來我的公司。寬闊的額頭,小而堅毅的眼睛,她告訴我這是我的父親。
那個時候的他還很年輕,愛上了一個女人,並和她生了一個孩子。2年後他背棄了她,娶了另一個女人,又生了一個孩子。在這個孩子六歲的時候,他回到了第一個女人身邊。
這簡直是一個傳奇,或者肥皂劇的劇情。然而這一切是如此的逼真,連他臉上的皺紋都加重了真實性。
第一個女人是清木的母親,第二個女人是我的母親。
兩個不幸的家庭。但是她不怪他,甚至在他描述時,充滿哀怨和憐憫的看著他。
我能夠說什麼呢?我想起了那個讓我一直害怕的眼睛,還想起了在黑暗裡和他唯一一次的見面。電光火石間的相逢,卻不認識是前身的宿命。
他是我同父異母的哥哥。
也許他的眼神裡不光只是殺機吧。他的父親這樣描述他:“從小他就是個堅強,但是也很固執的孩子,他很少說話,也沒有朋友,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我很想跟他說話,但是他離開了M縣自己謀生,他從不回來,也不寫信。直到……”
M縣那個母親曾經帶我去過一次的地方,荒涼的地方,大概是為了勸回父親吧。
清木其實有回去看過他,只是他不知道而已,我們發現了去M縣的車票,這是他最後一次去看沒有給自己名分的父親吧,當時他的心情會是怎麼樣呢?
一個從小被稱為私生子的孩子,一個從小被稱為豬的孩子,迅速的產生了友誼。兩個卑微而可憐的生命是冬天裡相擁取暖的孩子,他們有的僅僅是彼此的體溫吧。
清木有一段時間在我們學校當過零時工,從他父親的嘴裡模糊的推斷出。他說:“從外面打工回來的孩子說在S大學裡看見過清木。”
原來我們兄弟生活得如此接近,卻感覺不到彼此的呼吸。大概也是那個時候他認識了夏元吧。
他和他更為接近。
也許當我沐浴著陽光在草地上看書時,他在一邊埋頭掃地。也許在我和朋友勾肩搭背的時候,他在一邊獨自的吃著鹹菜和饅頭。
這是個春日的夜晚,有淡淡的月光漂浮在空氣裡,輕舞飛揚。我眺望遠方,霓虹燈披著五彩的沙巾,睜著半睡半醒的眼睛。
不知道明、宏翼、小飛他們過得怎麼樣了。往事也像月色一樣漂浮了起來,溢滿了我的心。
我微微一笑。
大地一個轉身。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