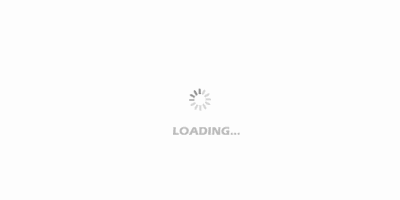從很大的程度上來看,赫耳墨斯學派的寫作者要表達的只是另一種版本的新柏拉圖主義思想。我們一眼就可以認出這種關於這種創造的進程系統。赫耳墨斯學派有一個版本叫做Poimandres,第一個流溢是Nous。Nous為陰陽合一,產出第二個流溢體Demiurge(德穆格),Demiurge產生七個governors,他們就是命運支配者和賦予者。人類的靈魂從Nous歷經七個governors後落於物質世界。在占星學理念中,每一個靈魂在出生時都有自己的特定的歸屬星座。
然後就是死亡,死後靈魂便脫離肉體經過七行星返回天國,每經歷一顆行星便丟棄相應的“枷鎖”。對文藝復興時期來說,
赫耳墨斯學派的文字中既有諾斯替思想中的悲觀成分,也有樂觀成分,可以說是兩者奇怪的融合。這同樣也說明了這篇東西是由許多不同的作者寫作而成。在有些篇章裡說道人的肉體是黑暗的監獄、囚禁靈魂的牢籠。但在另一些篇章裡卻強烈地趨向于樂觀派,提到萬物有靈、萬物皆神的思想。這種樂觀派的風格很可能就是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所寫,所以這篇東西產於文藝復興時期的跡象是越來越明顯。
萬物有靈的泛神論觀點使得新柏拉圖主義和神秘主義教派取得聯繫。上帝本身是超驗的,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們為什麼會將樂觀與悲觀的調和在一起,這點不是很清楚。物質同時擁有善與惡兩種特質,一個人既要為了束縛于肉體感到欣喜又要致力於實踐靈魂的提升。實際上,這種情況並非將兩種對立的要素進行調和,而僅僅只是簡單地接受這種看法,因為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們都知道這兩種對立的情況皆被Hermes提及過,所以他們就認為兩種觀點都是對的,因為其來自於偉大的赫耳墨斯,如果這個人無法理解其中的深意,至少他知道赫耳墨斯能夠理解,這便足矣。
在赫耳墨斯學派的文字中有許多細節都會使我們想到塔羅。比如赫耳墨斯的門徒Tat經歷了神秘主義的死亡與重生之旅,
在諾斯替神話裡,新柏拉圖主義中的Nous(奴斯,理智)被稱為Light(光),這讓我們想到從塔羅牌第16到19這段旅程。
正如最後一張大牌——世界的牌圖中所展示,Nous是陰陽合一體。在神秘主義的最高境界,就是超越二元,與Nous融為一體。所以世界牌圖中的陰陽合一形象就是代表著這種思想。在赫耳墨斯文集中,有寫到一段對話,
塔羅牌展現的是一組介於俗世與上帝之間的中間世界,在奴斯、邏各斯與造物主三位一體之下是各階天體。在天體之下則是埃及和希臘的各位神明以及各種抽象的理念。
Tarot Symbolism的作者Robert O’Neill層嘗試列出了塔羅牌與赫耳墨斯文集中各神明的對應。當然,這些對應只是嘗試性的,所以也就不列出了。不過這些對應即便很牽強,但至少說明了塔羅牌與那些神明一樣,都是一種仲介體,只不過塔羅牌是以符號象徵系統的形式來反映人類到Anima Mundi(世界靈魂)之間一級一級發展的“階梯”。
經過對塔羅漫長的學習,
所以這裡,我們必須指出,這裡所說的思想並不適用於塔羅設計者的系統結構,這個系統結構很大程度上吸取自赫耳墨斯文集。赫耳墨斯文集被帶回義大利並被費奇諾翻譯成拉丁文的時間是1460年,而塔羅出現的時間大約是14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