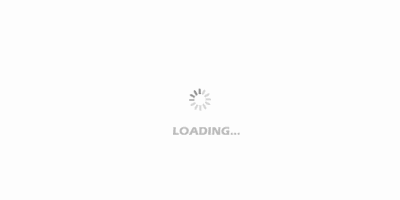五更八歲那年,獨自坐在村頭的大榕樹下默默地看著他想像中的天空發呆。一個足蹬麻鞋、身著一領破舊灰布袈裟、滿面紅光的化緣和尚恰巧路過這裡,和尚駐足端詳五更片刻,走上前去,一雙大手從五更的頭頂一直摸到腳趾,和尚微微一笑,點了點頭,五更竟用那烏黑的小手牽著和尚的衣角尾隨而去,從此杳無音信。
二十年後的一個冬天,五更伴隨著陣陣刺骨的寒風又回到了只剩下點滴記憶的家鄉。可惜五更的父母早已亡故,原有的幾間房屋、幾畝坡地也被伯父據為己有。五更在母親生前的好友三嬸的攙扶下來到父母的墳前,
天亮後,五更在三嬸的攙扶下來到離村三裡遠的一間破廟棲身,三嬸幫他打掃乾淨後,五更從背著的布袋子中拿出一尊放著金光、滿臉堆笑,坦露著個大肚皮的菩薩,恭恭敬敬地擺在廟中的石桌上,然後點上三炷檀香,五更又是俯身叩了三個響頭,帶得同來的三嬸也跟著叩了三個響頭。打那以後五更以廟為家,
三嬸是五更回來後最關心他的一個親人,三嬸問:“五更,這些年去了哪裡?”五更說;“浪跡天涯。”三嬸又問;“五更,你可曾成家?”五更答道:“四海為家。”三嬸再問:“五更,你怎麼不去找你大伯把你家的房子要回來,反倒一個人跑到這個破廟裡棲身呢?”五更說;“身外之物,無須看得太重,他們喜歡就由他們去吧!”聽得三嬸雲山霧罩的不得要領。三嬸心裡暗暗地想:五更八成是當了和尚,不然怎麼會成天對著個笑臉菩薩又是燒香又是念經?可你要說五更當了和尚吧,
一天中午,太陽曬得大地像火一樣發燙,山坡上的樹葉都卷了邊,躲在樹蔭裡的知了不停地吱——吱——地叫著,更增添了人們的煩躁。剛送完穀子到集市後回家的幾個壯後生實在熱得受不了,肩扛扁擔籮筐順著小路爬到五更住的破廟來討水喝,五更拿出來個葫蘆瓢指著一個名叫狗子的後生說:“你們都能喝就是這位施主不能喝。”狗子一聽伸長了脖子沖著五更喊:“和尚我和你往日無冤今日無仇,你為麼事就獨獨不給水我喝呢?”五更說:“施主聽我一句話,這水誰都能喝就是你不能喝。”狗子性子強,搶過同伴手中的瓢就要自己去舀水喝,
狗子一夥等到太陽偏西了才走,臨走狗子還說:“死瞎子你看我不是好好的麼,我家離這裡不到五裡地,我一會兒就到家了!”五更把他們幾個送出門還囑咐說:“快走吧,路上不要停,不然真的是到不了家呢!”
哥幾個一路有說有笑,走出三裡多路眼看前面就是自己村子了,突然狗子感到一陣陣心絞痛,氣都喘不過來,臉色一下子就變得慘白,其它幾個慌了,這才想起五更說的“不快點走到不了家”的話。趕緊讓狗子躺在路邊,叫一個後生跑著去找五更。
這件事被幾個後生越傳越神,說五更有先見之明,能知人生死。三嬸找到廟裡問五更,五更淡淡地說:“哪有那麼神,我只是抓住他手腕的時侯從他的脈搏上覺察出來他得了急病,這種病如果是熱人被涼水一浸神仙也沒辦法救他了。”可同狗子一起去的幾個後生卻說,五更一開始就不給水狗子喝,是狗子搶瓢的時侯五更才抓住狗子的手,五更肯定是一進門就知道狗子要死,只不過他不好明說罷了。
這件事情傳到五更大伯的耳朵裡,他不信五更真的遇到什麼高人,得到什麼真傳,如果真的有先見之明,能知人生死,那他還不早就把他家的房子奪了回去?還用得著跑到破廟裡與清風為伴,與日月為鄰嗎?但五更的出現確實是他的一塊心病,他決定試一試五更到底有沒有人們說的那麼邪乎。
這天一大清早,五更的大伯就叫人把三嬸領進了他的臥室,三嬸朝床上一看,兩床厚厚的棉被下,只露出一個隻剩幾根稀疏白髮的腦袋,只有偶爾眨動著的那雙渾濁的眼睛還能看出躺在床上的是個活物,活物有氣無力地對三嬸說:“他三嬸,我不知道怎麼突然就覺得心口像刀子鉸一樣,我看恐怕是閻王爺要我去報到了,你能不能幫我去廟裡請一下五更,叫他看在祖宗的份上救老夫一命。”說完眼睛一閉,頭往旁邊一歪,好像立馬就要斷氣似的。三嬸一看這是救人命的大事,哪裡還能說個不字,起身就往五更那裡趕。
三嬸一走,大伯的兩個兒子從側門哈哈大笑著走了出來,老大說:“爹,你可真會演戲,連我們都看不出一點破綻來,五更那個瞎子他還能不上當?”老二說:“爹,你先下床歇會吧,大熱的天別在被子裡捂壞了。”老人搖了搖頭說:“要裝就裝它個天衣無縫,萬一要是五更突然闖了進來,那這曲戲不就穿了幫?”
三嬸走後,老人躺在床上吃也不敢起來吃,只是叫兩個兒子一會兒喂一次水,一會兒喂一次水,尿急了也不敢起來拉。好不容易等到太陽快下山了三嬸才牽著五更進了門。五更坐到床邊,拿起大伯的左手伸出三個指頭搭在脈門上,片刻後站了起來對三嬸說:“準備料理後事吧。”
五更的話剛說完,老大和老二從側門走了出來,老大拍著巴掌笑著說:“精彩!真精彩!五更,你別再裝神弄鬼了,我爹他根本就沒病,只不過是想試一下你到底有多深的道行。我看你比你娘老子還好騙。爹,你起來叫瞎子五更看看,我們要不要跟你料理後事!哈哈哈哈!”
五更頭也沒回繼續往外走,又說了一句:“準備給你爹料理後事吧。”兩兄弟這下可不依了,扯住五更不讓走,硬說五更是咒他老子,一定要五更賠罪。五更兩膀一用力甩開這哥倆說“實話跟你倆說吧,老人家原本是沒有病,但是這大熱天不排尿,尿毒已經攻心了,快去跟你爹多說幾句話吧,不然再想和你爹說話可就要等到下輩子了。”
聽五更這麼一說,哥倆趕緊跑到床邊,老人用那已經開始發散的目光看著兩個兒子斷斷續續地說:“報應,報應哪!當年我為了霸佔他家的房產,設計害死了他的父母,我想過我的很多種死法,就是沒想到竟是這樣自己要了我自己的命哪!”老人說完兩腿一伸,真的死了。
從這以後,五更的破廟不再冷清了,隔三差五有人上來找他,不是看日子,測八字,就是問流年,問前程,問財運,也有的是來請五更上門“化解”厄運的,但更多的人是來尋醫問藥。凡是算過命的只說一個字“准”;凡是疹過病的也是只有一個字“靈”。五更來者不拒,有求必應,錢不論多少,聽憑來人佈施。
幾年以後,五更請人在原來破廟的地基上重新蓋起了一座高大的寺廟,重新塑了一尊大的笑臉菩薩,還叫人用楠木雕刻了一副 “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口便笑笑世間可笑之人”的對聯掛在菩薩兩邊,使廟裡無形中又多了幾分肅穆。
五更叫人在寺廟大門的上方掛了一塊五尺多長的楠木大扁,雖然漆得油光發亮,上面卻沒有一個字。凡是來寺廟裡的人都要問五更為什麼掛個沒有字的扁在大門上。五更只是淡淡地一笑,從不作答。人們只好憑自己的愛好有的叫它彌勒寺,有的叫它大肚笑臉菩薩廟,還有的乾脆叫它無字廟。不管人們怎麼叫五更還是淡淡一笑,從不反對,也不贊成。反正從此以後五更所在的廟裡香火一日盛似一日,五更的名聲也越傳越遠。
寺廟建好後不久,五更去了一趟城裡,回來時領著一個十幾匹馬的馬幫,馬背兩邊的麻袋裝得鼓鼓的。第二天五更叫三嬸找幾個聰明伶俐的小後生哥到廟裡幫忙,講明瞭工錢是沒有的,只是管飯。三嬸現在最信五更了,回村就把自家的幾個侄兒叫了來。自己也到廟裡幫五更做飯。一行人起五更睡半夜的忙了半個多月,把馬幫駝回的二十幾麻袋藥材全部按五更的吩咐切的節輾的輾,再包成一個一個的小包,然後又用麻袋裝好。三嬸發現五更配的藥都是一樣的方子,一樣的劑量,就忍不住問五更,五更搖了搖頭不肯說,問急了也只是說這是天機不能洩露。完工那天五更拿出幾包藥來分給大家,並反復說一定要把藥放好,到要命的時侯喝了可以救命。
在這以後五更又進了兩趟城,又駝回兩次藥,又叫三嬸他們幫了兩次忙,又送了兩次藥給他們。三嬸說:“五更,你送這麼多藥給我們,一不告訴我們這藥疹什麼樣病,二不對我們講什麼時侯吃,我們又不開藥鋪,要這麼多的藥有麼用?”五更歎了一口氣說:“唉!到時侯不嫌少就阿彌陀佛了!”
半年以後就是中國農曆丁亥年,從正月初一開始方圓百里就沒下過一滴雨,這一年顆粒無收,各家各戶的存糧也都見了底,挨到第二年清明,按說該到了多雨水的季節了吧,可老天爺卻照樣日出日落,萬里無雲。人們開始靠挖野菜填肚子。可是時間旱得太久,野菜也少得可憐,要不了多久人們就開始吃樹葉、啃樹皮,挨到八月,一眼看到的都是白花花、光禿禿的樹權子,整個大地都沒有了一點點生氣。有人開始吃“貓兒泥”(現在的學名叫觀音土,是黃泥中夾著的一種灰色的泥土)餓極了的人們瘋子似的到處刨坑,從黃土層中一點一點地挑出灰色的粉末,如獲至寶般捧回家化成糊糊喝了下去,說來也怪,這“貓兒泥”喝進肚子裡後,人就不覺得餓了,而且一兩天都不想吃東西,大家以為有活路了老人、孩子,只要是人都開始吃“貓兒泥”。
幾天以後禍事來了,凡是吃了“貓兒泥”的一個個的肚子硬得像石頭,就是拉不出屎來,有人竟被活活地憋死了。三嬸一家人也吃了這要命的“貓兒泥”也憋得要死。三嬸突然想起五更送給她的幾包藥,就趕緊打開一包用水煎開喝了下去。沒想到喝下不到半個時辰,三嬸的肚子裡發也一陣咕嚕咕嚕的響聲,還沒等到三嬸爬到茅房,一泡稀湯屎全都拉在了褲子裡。肚子一松,人的精神一振,三嬸一下子從地上爬了起來,也不管褲襠裡的屎,趕緊又拿出一包五更給的藥煎上,每人一碗灌了下去,一家人終於從死神門口又撿回了性命。
三嬸想起上次和她一起去幫忙的幾個侄兒家也有這種藥,就急急忙叫他們也煎著喝,不到一個時辰的功夫,村裡人都知道三嬸有救命的藥,都來求三嬸,三嬸心也好架起一口大鍋熬好了一人一碗,一村的人都把三嬸當成了救命的女菩薩,跪在地上給三嬸叩頭,三嬸卻說這藥是五更給的,他才是救命的活佛。
消息一傳十十傳百,五更的廟前很快就排起了長隊,周圍百里凡是吃了“貓兒泥”的人都來找五更救命,五更早就叫三嬸和她的幾個侄兒在廟前架起三口大鍋,來的人先喝一碗藥,腸肚空了後再拿藥回家。那段時間,整條路上人來人往,來的都是雙手捂著肚子步履蹣跚,去的則是懷揣藥包疾步而行,個個恨不得把五更當神仙供起來!
災後不久,三嬸和那些九死一生的百姓,划船到五更那小廟裡來拜佛還願。到了小廟的山腳下,眾人下了船,沿著小路慢慢上山,一路上空氣中彌漫著一股股眾人所熟悉的、久違了的、祥和的檀香味,耳邊傳來聲聲不緊不慢的木魚聲。日光是那樣的和麗,輕風格外的輕柔,一行人個個覺得神清氣爽,如登蓬萊仙境一般。
眾人來到廟前,五更已步出廟門相迎。小玉人小眼快,指著廟門上那塊原本無字的楠木大扁大聲叫了起來:“你們快看,那大扁上有字了耶!”眾人順著小玉的手指仰頭朝那大扁望去,蒼勁有力的“雞鳴寺”三個鬥大的顏書清清楚楚地出現在那大扁上,使小廟平添了幾分肅穆與莊嚴之氣。
“好了!五更師傅的廟終於有名字了!”“雞鳴寺。這名字好哇,雞鳴報曉,說明五更師傅這寺廟能給我們眾生帶來光明,送來祥和呢!”人群中有一位教私塾的老先生,他朝大扁默默地看了半晌,問五更道:“五更師傅,這字是何人所題呀?”“阿彌陀佛!貧僧也不知這扁是何人何時所題。”老先生沉呤片刻說“按理說,這扁應由官府或民間德高望重之賢達所書,扁上之字理應鍍以金粉,且有題扁之人的落款,可這扁上之字不僅未用金粉甚至連墨都未用,好像是用手指鏤成,也無題扁之人的落款,真是有違常理呀!”
聽了老先生的一番話,五更心裡想:能在夜深人靜之時,逃過他那非常聽力,在這楠木扁上鏤成三個鬥大字的人,絕非等閒之輩。既然此人不願留下姓名,必定有他的道理。唉!區區一塊扁何必去深究呢?於是五更對眾人說道:“想當初修建這寺院之時,貧僧就沒有想過要給小寺題名,我只不過是以菩提心為本,大悲心為用,遵師所囑,‘己雖覺,還要覺他,己未覺,先要渡人’而已,既然小寺已得名‘雞鳴寺’,我看還是隨緣吧!”不過三嬸心裡明白,這雞鳴之時也正是五更來到人世的時刻。
打這以後,雞鳴寺的香火又慢慢地興盛了起來。一天,三嬸堅決要把小玉留在寺中,五更依舊不允,五更對三嬸說:“佛與凡人,佛與智聖之人只是”覺“與”迷“一字之差,佛不在天上,佛在各自心中,一燈能除千年暗,只要明心見性,無需出家,人人都能立地成佛。”怎奈三嬸和小玉向佛之心如鐵,尤其是小玉立意不肯回家。三嬸對五更說:“五更哪,你說的那些太深奧,三嬸聽不明白。但佛家講的是普渡眾生吧?你收小玉在寺中參禪修佛難道就不是普渡眾生麼?再說你一個盲眼之人,寺中香火又是日盛一日,總得要人打理吧?你既不肯收小玉為徒我也不強求於你,就讓小玉與你有師徒之實而無師徒之名總行了吧?”三嬸的這一番話至情至理,五更不好再推辭。從此小玉就留在了雞鳴寺。
五更兩次未卜先知,救生靈於水火的事越傳越遠,越傳越神,傳到了兩榜進士出身的放任知府謝進才的耳朵裡,再加上雞鳴寺所在縣令呈報:本縣向佛之風日盛,民眾多行善舉,頑劣之徒幾乎絕跡。更引起了這位剛上任的知府大人的興趣。他決定和縣令一道微服私訪雞鳴寺。
這天,謝知府在縣令的陪同下,只帶兩名貼身待衛,一行人身穿便服來到雞鳴寺一探究竟。到了寺前,只見除了出出進進的香客外,還有人排成一隊挨個等侯。知縣悄聲告訴謝知府這些都是來找五更看病的百姓。知府哦了一聲,抬頭看著扁上的三個大字,扭頭問跟在身後的縣令:“此扁為何人所題?”縣令答道:“不知何人所題。大人可否看出此扁有什麼不妥?”“不是不妥,而是題扁之人不僅書法造詣爐火純青,功力也非同一般哪!”
一行人緩步走進廟門,見一光頭和尚坐在一張舊木桌後正眯著眼在給人看病,謝知府停住腳步認真地上下打量著這個身著灰布僧衣, 貌不驚人的瞎眼和尚。在他心裡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這眼前的和尚與人們傳說的“神僧”劃上等號。他甚至懷疑人們是不是以訛傳訛。
正在謝知府觀察五更給人看病時,寺門外傳來一片嘈雜的叫喊聲,一個大漢攙扶著一個中年女子走進了廟門,女人兩手卡在腰間,雙肩歪向一邊,嘴裡不斷地發出“哎喲!哎喲!”的痛苦呻吟。大漢一邊用手撥開眾人一邊焦急地朝眾人點著頭說:“讓一下,麻煩讓一下。”眾人雖有不滿,但看那女人疼痛難忍的樣子也就紛紛避讓在一旁。大漢把女人扶到桌前坐下,一邊用衣袖擦著臉上的汗一邊焦急地對五更說:“師傅,你快救救我媳婦吧,好好的腰,怎麼說痛就痛得受不了呢?八成是斷了,你一定要幫我救救她,我家裡還有個吃奶的孩子靠她奶大呢!”
五更聽大漢一說,摸著桌邊來到女人的背後,叫女人站了起來。五更伸手緩緩地摸了摸女人的腰,突然他扯住女人的褲腰往下一拉,頓時露出女人腰間三寸多寬的白肉來,女人殺豬也似一聲尖叫,一手提著褲腰一手掩著臉,起身就往寺外跑去。在眾人的哈哈大笑聲中,大漢先是一楞,接著拔腿就往外追趕媳婦去了。就在五更準備繼續給人看病的時侯,大漢手舉一根碗口粗的木棍大步走了進來,口中大聲罵道:“你這禿驢,竟敢在眾目睽睽之下調戲我媳婦,看我不打爛你這禿瓢!”五更緩緩站了起來念了聲阿彌陀佛!對大漢說:“施主請不要動怒,貧僧問你,你帶你媳婦是來幹什麼的?”大漢說:“來治腰痛的呀!”五更說:“那不就對了。你再看看你媳婦的腰好了沒有?”大漢一扭頭,只見自己的媳婦正雙手緊緊地抱著他舉起的木棍,低著頭朝他埋怨說:“你還不向五更師傅賠禮!你看,我這腰一點都不痛了!”大漢不信,硬是叫媳婦當著眾人試給他看,媳婦羞得滿臉通紅,照著丈夫說的左扭扭右擺擺,與來時判若兩人,她嬌嗔地對丈夫說:“你看這不是眨眼的工夫全好了嗎?一點都不痛呢!”大漢丟下手中的木棍,雙膝一跪,朝著五更叩起了響頭。逗得殿內拜佛的,燒香還願的,看病的眾人又一陣開心的哈哈大笑。
謝知府和同來的一行人也看得樂了,跟著眾人一通開懷大笑後。謝知府上前一步走到桌子對面坐了下來,看著五更問:“敢問師傅,你是如何得知這婦人的腰傷能用此法治好的呢?”五更若有所思,沉呤片刻,站起身來朝謝知府一低頭念了一聲阿彌陀佛說:“多謝施主屈尊光臨雞鳴小寺,貧僧這方有禮了!其實這婦人腰傷只不過是難者不會而已。聽她丈夫所言,貧僧已經知道婦人這傷是新傷而非陳年舊傷。貧僧一摸婦人腰間,見其骨胳健壯,同時摸到婦人身著粗布衣衫,因而貧僧斷定婦人乃是勞作之人,斷不會患淫逸之傷,必是突然扭傷所至,其實她自己只要多彎腰活動就可痊癒。可婦人大都耐不住疼痛,貧僧只好出此不雅之下策了。阿彌陀佛!”
五更一席話說得滿殿的人個個點頭,人人稱妙。謝知府既不點頭也不稱妙,繼櫝問道:“和尚本應拜佛誦經,師傅為何不去誦經卻給人治病呢?”五更答道:“我佛慈悲,普渡眾生脫離苦海,人生有八苦,肉生占其四,尤其以病為最苦,貧僧只不過是積小善為大善,積小德為大德,助人脫離病痛之苦不就是最起碼的普渡眾生麼?”謝知府又問五更:“那師傅看我有何病症?”五更又沉呤片刻緩緩答道:“施主暫無大礙。”“那何時有礙呢?”“三年以後。”“有何礙?”“白!”“何為白?”謝知府緊追著問五更,五更依然是緩緩而言:“此乃天機不可明言,施主只須牢記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定保無事!”
聽了五更的話,謝知府心中一驚,三年之後有無大礙他可以不信,在他眼裡和尚、道士大多故弄懸殊,真正道行高深者、立地成佛者能有幾人?可他就不明白,自己一行人自進這寺門並未露出什麼破綻,可五更一個瞎眼之人,怎麼就知道自己是個做官的呢?謝知府還在滿腹狐疑,五更又說話了:“大人是不是正在想貧僧是怎麼識破大人身份的事呀?
這個其實不難,無須大人這樣絕頂聰明的人去費心力。大人的心力須用在治下百姓身上才是。好了,你我今日已有一面之緣了,大人請回吧,貧僧還要為眾人解除病痛之苦呢!煩請大人記住貧僧今日所言,不然大人恐有性命之憂!”
打雞犬不寧鳴寺回來後,謝進才還時不時想起五更說的話,為官還算是清正廉明,四方百姓也能安居樂業。可太平日子一久,知府覺得做地方官也不過如此,這身體也沒見起什麼變化,神僧說的也不見得就准。漸漸地謝進才把五更說過的話扔到了一邊,再也不去想它了。
謝進才這一放鬆不打緊,骨子裡原本就有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貪婪之心就不知不覺地膨脹了起來。先小貪,後大貪,先是自己貪,後是手下各級官吏一齊貪。把一個原本清平安樂的治下攪得烏煙瘴氣,民不聊生,百姓個個苦不堪言。
說來也怪,這謝進才貪的銀子越多,他的肚子也慢慢地變得越來越大,開始還不覺得是個累贅,還真的以為是屬下拍馬所說的那樣——發福,誰知三年後肚子竟如小禾桶一般,別說是行走,就是到前衙審案也要四個大漢把他抬到文案後的太師椅上去,而且還不時隱隱作痛。謝進才遍請名醫診治,卻不見有絲毫消退。反而一日比一日大。這天謝進才終於倒在後衙的地上,肚子內有如刀絞火燎一般, 痛得他殺豬一般嚎叫。請來的名醫聖手個個看了只是搖頭,悄悄地叫他的家人準備後事。
正當眾人束手無策的時侯,當年陪同謝進才私訪雞鳴寺的縣令想起了五更說的“三年以後”的話,也記起五更當年曾說的一個“白”字,難道這個“白”是指白花花的銀子?難道知府大人的怪病是由貪銀而引起的?想到這裡縣令倒吸了一口冷氣,嚇得出了一身的冷汗,不由得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肚皮,此時他才後悔這幾年跟著謝知府也變成了一個千夫所指的貪官。
縣令把自己的想法對知府一說,謝進才也如夢初醒,縣令立即叫人紮了一乘軟轎,挑了幾名身高體壯的兵丁,抬著已經無力嚎叫仍在痛苦呻吟的知府大人,火急火燎地趕到了雞鳴寺。縣令拉著五更的衣袖也顧不得臉面和身份,不住地哀求著說:“五更師傅,五更活菩薩,你快出手救救知府大人的命吧,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哇!”
五更來到擺放在地上的謝進才身邊,彎下腰用手按了按他的肚皮說:“阿彌陀佛,施主可曾記得貪僧三年前說過的話麼?”知府用那雙死魚般的眼睛看著五更,無力地點了點頭。五更伸直了腰,像是對知府也像是對眾人,更像是發自內心的感悟,他緩緩地說道“我為僧者,是秉承佛祖旨意,慈悲為懷,普渡眾生,你為官者,秉承聖意應清正廉明,懲惡揚善。二者雖途不同則歸一至。佛與凡人並不遙遠,僅一字之遙。”覺“者成佛,”迷“者為人。但願”迷“者早日知返。阿彌陀佛!”
五更的一番話只聽得知府一班人如雞吸米般地點頭,這是他們第一次聽說佛與人的區別,第一次感受到心靈是如此的震憾。縣令還是忘不了他那躺在地上的上司,又拉住五更的袖子搖了搖說:“大師,請你快點動手吧,不然就來不及了呀!”五更大聲叫了聲:“玉兒,取針來。”隨即又對縣令說:“還是把這位施主抬到寺外的蔭涼處吧,不要汙了佛門清靜之地。”
一行人七手八腳地將知府抬到寺門外的大樹下,人們也都跟著像看耍猴一樣把知府圍在了圓圈中間。五更叫眾人往後退開幾步,彎下腰,接過小玉遞過來的一根二尺來長的竹針,照著知府的肚臍眼紮了下去。知府大叫一聲:“哎喲,痛煞我也!”兩眼一翻,竟昏死了過去。五更用右手的兩個指頭不停地撚動著手中的竹針,片刻工夫,竹針只剩下寸許露在知府的肚臍眼上,就像是一根剛燒完的香枝。眾人看得大氣都不敢出,四周一片寂靜。
就在這時,知府肚臍上的竹針自己擺動了起來。五更伸手捏住那擺動的竹針,大喝一聲:“出來吧!”右手一揚,將竹針拔了出來。竹針一撥,知府的肚臍眼“撲”的一聲,噴出一道黃黃的噴泉,一股刺鼻的醒臭味刹時彌漫開來。眾人不由得捂住鼻子朝後退讓。
這臭水一出,知府的肚子自然也就癟了。只見知府睜開雙眼,長長地出了一口氣,他雙手一按地坐了起來,環顧四周問:“我可是到了陰間?”縣令趕緊忙上前一把扶住知府,在他耳邊說:“恭喜大人,賀喜大人,五更師傅把你從陰間又救回了陽世,你的肚子已經消了。”知府這才想起自己的肚子,用手一摸,什麼話也不說翻身就跪在地上朝五更叩起了響頭。
就在這時,只聽眾人“哇”的一聲驚叫,知府肚子裡噴出來灑落在青石板上的臭水,竟在那青石板上形成了一個個白色的元寶圖案。五更叫人拿來鋤頭撬起這塊有元寶的青石,念了一聲阿彌陀佛!對知府說道:“佛祖葆佑,施主已無大礙了,這塊石板施主就請拿回去做個紀念吧!”
一行人又抬著知府走了,真的是把那塊青石板也抬走了。不久這塊有著“元寶”的青石出現在知府衙門的壁照下,背面多了兩個血也似的鮮紅大字“戒貪”。據說,打這以後歷任的知府再也沒有出一個貪官。士、農、工、商又各執其事,庶民百姓又能安居樂業!這是後話。
謝知府和一班貪官經此一折騰後,個個膽顫心驚,紛紛吐出了所貪的不義之財。眾官決定將這筆銀兩全部捐給雞鳴寺,可等他們一行人來到雞鳴寺時,寺中只有小玉一人,小玉說師傅已下山雲遊一個多月了,何時回來不得而知。五更去了哪裡,誰也不知道。
只不過他不好明說罷了。
這件事情傳到五更大伯的耳朵裡,他不信五更真的遇到什麼高人,得到什麼真傳,如果真的有先見之明,能知人生死,那他還不早就把他家的房子奪了回去?還用得著跑到破廟裡與清風為伴,與日月為鄰嗎?但五更的出現確實是他的一塊心病,他決定試一試五更到底有沒有人們說的那麼邪乎。
這天一大清早,五更的大伯就叫人把三嬸領進了他的臥室,三嬸朝床上一看,兩床厚厚的棉被下,只露出一個隻剩幾根稀疏白髮的腦袋,只有偶爾眨動著的那雙渾濁的眼睛還能看出躺在床上的是個活物,活物有氣無力地對三嬸說:“他三嬸,我不知道怎麼突然就覺得心口像刀子鉸一樣,我看恐怕是閻王爺要我去報到了,你能不能幫我去廟裡請一下五更,叫他看在祖宗的份上救老夫一命。”說完眼睛一閉,頭往旁邊一歪,好像立馬就要斷氣似的。三嬸一看這是救人命的大事,哪裡還能說個不字,起身就往五更那裡趕。
三嬸一走,大伯的兩個兒子從側門哈哈大笑著走了出來,老大說:“爹,你可真會演戲,連我們都看不出一點破綻來,五更那個瞎子他還能不上當?”老二說:“爹,你先下床歇會吧,大熱的天別在被子裡捂壞了。”老人搖了搖頭說:“要裝就裝它個天衣無縫,萬一要是五更突然闖了進來,那這曲戲不就穿了幫?”
三嬸走後,老人躺在床上吃也不敢起來吃,只是叫兩個兒子一會兒喂一次水,一會兒喂一次水,尿急了也不敢起來拉。好不容易等到太陽快下山了三嬸才牽著五更進了門。五更坐到床邊,拿起大伯的左手伸出三個指頭搭在脈門上,片刻後站了起來對三嬸說:“準備料理後事吧。”
五更的話剛說完,老大和老二從側門走了出來,老大拍著巴掌笑著說:“精彩!真精彩!五更,你別再裝神弄鬼了,我爹他根本就沒病,只不過是想試一下你到底有多深的道行。我看你比你娘老子還好騙。爹,你起來叫瞎子五更看看,我們要不要跟你料理後事!哈哈哈哈!”
五更頭也沒回繼續往外走,又說了一句:“準備給你爹料理後事吧。”兩兄弟這下可不依了,扯住五更不讓走,硬說五更是咒他老子,一定要五更賠罪。五更兩膀一用力甩開這哥倆說“實話跟你倆說吧,老人家原本是沒有病,但是這大熱天不排尿,尿毒已經攻心了,快去跟你爹多說幾句話吧,不然再想和你爹說話可就要等到下輩子了。”
聽五更這麼一說,哥倆趕緊跑到床邊,老人用那已經開始發散的目光看著兩個兒子斷斷續續地說:“報應,報應哪!當年我為了霸佔他家的房產,設計害死了他的父母,我想過我的很多種死法,就是沒想到竟是這樣自己要了我自己的命哪!”老人說完兩腿一伸,真的死了。
從這以後,五更的破廟不再冷清了,隔三差五有人上來找他,不是看日子,測八字,就是問流年,問前程,問財運,也有的是來請五更上門“化解”厄運的,但更多的人是來尋醫問藥。凡是算過命的只說一個字“准”;凡是疹過病的也是只有一個字“靈”。五更來者不拒,有求必應,錢不論多少,聽憑來人佈施。
幾年以後,五更請人在原來破廟的地基上重新蓋起了一座高大的寺廟,重新塑了一尊大的笑臉菩薩,還叫人用楠木雕刻了一副 “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口便笑笑世間可笑之人”的對聯掛在菩薩兩邊,使廟裡無形中又多了幾分肅穆。
五更叫人在寺廟大門的上方掛了一塊五尺多長的楠木大扁,雖然漆得油光發亮,上面卻沒有一個字。凡是來寺廟裡的人都要問五更為什麼掛個沒有字的扁在大門上。五更只是淡淡地一笑,從不作答。人們只好憑自己的愛好有的叫它彌勒寺,有的叫它大肚笑臉菩薩廟,還有的乾脆叫它無字廟。不管人們怎麼叫五更還是淡淡一笑,從不反對,也不贊成。反正從此以後五更所在的廟裡香火一日盛似一日,五更的名聲也越傳越遠。
寺廟建好後不久,五更去了一趟城裡,回來時領著一個十幾匹馬的馬幫,馬背兩邊的麻袋裝得鼓鼓的。第二天五更叫三嬸找幾個聰明伶俐的小後生哥到廟裡幫忙,講明瞭工錢是沒有的,只是管飯。三嬸現在最信五更了,回村就把自家的幾個侄兒叫了來。自己也到廟裡幫五更做飯。一行人起五更睡半夜的忙了半個多月,把馬幫駝回的二十幾麻袋藥材全部按五更的吩咐切的節輾的輾,再包成一個一個的小包,然後又用麻袋裝好。三嬸發現五更配的藥都是一樣的方子,一樣的劑量,就忍不住問五更,五更搖了搖頭不肯說,問急了也只是說這是天機不能洩露。完工那天五更拿出幾包藥來分給大家,並反復說一定要把藥放好,到要命的時侯喝了可以救命。
在這以後五更又進了兩趟城,又駝回兩次藥,又叫三嬸他們幫了兩次忙,又送了兩次藥給他們。三嬸說:“五更,你送這麼多藥給我們,一不告訴我們這藥疹什麼樣病,二不對我們講什麼時侯吃,我們又不開藥鋪,要這麼多的藥有麼用?”五更歎了一口氣說:“唉!到時侯不嫌少就阿彌陀佛了!”
半年以後就是中國農曆丁亥年,從正月初一開始方圓百里就沒下過一滴雨,這一年顆粒無收,各家各戶的存糧也都見了底,挨到第二年清明,按說該到了多雨水的季節了吧,可老天爺卻照樣日出日落,萬里無雲。人們開始靠挖野菜填肚子。可是時間旱得太久,野菜也少得可憐,要不了多久人們就開始吃樹葉、啃樹皮,挨到八月,一眼看到的都是白花花、光禿禿的樹權子,整個大地都沒有了一點點生氣。有人開始吃“貓兒泥”(現在的學名叫觀音土,是黃泥中夾著的一種灰色的泥土)餓極了的人們瘋子似的到處刨坑,從黃土層中一點一點地挑出灰色的粉末,如獲至寶般捧回家化成糊糊喝了下去,說來也怪,這“貓兒泥”喝進肚子裡後,人就不覺得餓了,而且一兩天都不想吃東西,大家以為有活路了老人、孩子,只要是人都開始吃“貓兒泥”。
幾天以後禍事來了,凡是吃了“貓兒泥”的一個個的肚子硬得像石頭,就是拉不出屎來,有人竟被活活地憋死了。三嬸一家人也吃了這要命的“貓兒泥”也憋得要死。三嬸突然想起五更送給她的幾包藥,就趕緊打開一包用水煎開喝了下去。沒想到喝下不到半個時辰,三嬸的肚子裡發也一陣咕嚕咕嚕的響聲,還沒等到三嬸爬到茅房,一泡稀湯屎全都拉在了褲子裡。肚子一松,人的精神一振,三嬸一下子從地上爬了起來,也不管褲襠裡的屎,趕緊又拿出一包五更給的藥煎上,每人一碗灌了下去,一家人終於從死神門口又撿回了性命。
三嬸想起上次和她一起去幫忙的幾個侄兒家也有這種藥,就急急忙叫他們也煎著喝,不到一個時辰的功夫,村裡人都知道三嬸有救命的藥,都來求三嬸,三嬸心也好架起一口大鍋熬好了一人一碗,一村的人都把三嬸當成了救命的女菩薩,跪在地上給三嬸叩頭,三嬸卻說這藥是五更給的,他才是救命的活佛。
消息一傳十十傳百,五更的廟前很快就排起了長隊,周圍百里凡是吃了“貓兒泥”的人都來找五更救命,五更早就叫三嬸和她的幾個侄兒在廟前架起三口大鍋,來的人先喝一碗藥,腸肚空了後再拿藥回家。那段時間,整條路上人來人往,來的都是雙手捂著肚子步履蹣跚,去的則是懷揣藥包疾步而行,個個恨不得把五更當神仙供起來!
災後不久,三嬸和那些九死一生的百姓,划船到五更那小廟裡來拜佛還願。到了小廟的山腳下,眾人下了船,沿著小路慢慢上山,一路上空氣中彌漫著一股股眾人所熟悉的、久違了的、祥和的檀香味,耳邊傳來聲聲不緊不慢的木魚聲。日光是那樣的和麗,輕風格外的輕柔,一行人個個覺得神清氣爽,如登蓬萊仙境一般。
眾人來到廟前,五更已步出廟門相迎。小玉人小眼快,指著廟門上那塊原本無字的楠木大扁大聲叫了起來:“你們快看,那大扁上有字了耶!”眾人順著小玉的手指仰頭朝那大扁望去,蒼勁有力的“雞鳴寺”三個鬥大的顏書清清楚楚地出現在那大扁上,使小廟平添了幾分肅穆與莊嚴之氣。
“好了!五更師傅的廟終於有名字了!”“雞鳴寺。這名字好哇,雞鳴報曉,說明五更師傅這寺廟能給我們眾生帶來光明,送來祥和呢!”人群中有一位教私塾的老先生,他朝大扁默默地看了半晌,問五更道:“五更師傅,這字是何人所題呀?”“阿彌陀佛!貧僧也不知這扁是何人何時所題。”老先生沉呤片刻說“按理說,這扁應由官府或民間德高望重之賢達所書,扁上之字理應鍍以金粉,且有題扁之人的落款,可這扁上之字不僅未用金粉甚至連墨都未用,好像是用手指鏤成,也無題扁之人的落款,真是有違常理呀!”
聽了老先生的一番話,五更心裡想:能在夜深人靜之時,逃過他那非常聽力,在這楠木扁上鏤成三個鬥大字的人,絕非等閒之輩。既然此人不願留下姓名,必定有他的道理。唉!區區一塊扁何必去深究呢?於是五更對眾人說道:“想當初修建這寺院之時,貧僧就沒有想過要給小寺題名,我只不過是以菩提心為本,大悲心為用,遵師所囑,‘己雖覺,還要覺他,己未覺,先要渡人’而已,既然小寺已得名‘雞鳴寺’,我看還是隨緣吧!”不過三嬸心裡明白,這雞鳴之時也正是五更來到人世的時刻。
打這以後,雞鳴寺的香火又慢慢地興盛了起來。一天,三嬸堅決要把小玉留在寺中,五更依舊不允,五更對三嬸說:“佛與凡人,佛與智聖之人只是”覺“與”迷“一字之差,佛不在天上,佛在各自心中,一燈能除千年暗,只要明心見性,無需出家,人人都能立地成佛。”怎奈三嬸和小玉向佛之心如鐵,尤其是小玉立意不肯回家。三嬸對五更說:“五更哪,你說的那些太深奧,三嬸聽不明白。但佛家講的是普渡眾生吧?你收小玉在寺中參禪修佛難道就不是普渡眾生麼?再說你一個盲眼之人,寺中香火又是日盛一日,總得要人打理吧?你既不肯收小玉為徒我也不強求於你,就讓小玉與你有師徒之實而無師徒之名總行了吧?”三嬸的這一番話至情至理,五更不好再推辭。從此小玉就留在了雞鳴寺。
五更兩次未卜先知,救生靈於水火的事越傳越遠,越傳越神,傳到了兩榜進士出身的放任知府謝進才的耳朵裡,再加上雞鳴寺所在縣令呈報:本縣向佛之風日盛,民眾多行善舉,頑劣之徒幾乎絕跡。更引起了這位剛上任的知府大人的興趣。他決定和縣令一道微服私訪雞鳴寺。
這天,謝知府在縣令的陪同下,只帶兩名貼身待衛,一行人身穿便服來到雞鳴寺一探究竟。到了寺前,只見除了出出進進的香客外,還有人排成一隊挨個等侯。知縣悄聲告訴謝知府這些都是來找五更看病的百姓。知府哦了一聲,抬頭看著扁上的三個大字,扭頭問跟在身後的縣令:“此扁為何人所題?”縣令答道:“不知何人所題。大人可否看出此扁有什麼不妥?”“不是不妥,而是題扁之人不僅書法造詣爐火純青,功力也非同一般哪!”
一行人緩步走進廟門,見一光頭和尚坐在一張舊木桌後正眯著眼在給人看病,謝知府停住腳步認真地上下打量著這個身著灰布僧衣, 貌不驚人的瞎眼和尚。在他心裡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這眼前的和尚與人們傳說的“神僧”劃上等號。他甚至懷疑人們是不是以訛傳訛。
正在謝知府觀察五更給人看病時,寺門外傳來一片嘈雜的叫喊聲,一個大漢攙扶著一個中年女子走進了廟門,女人兩手卡在腰間,雙肩歪向一邊,嘴裡不斷地發出“哎喲!哎喲!”的痛苦呻吟。大漢一邊用手撥開眾人一邊焦急地朝眾人點著頭說:“讓一下,麻煩讓一下。”眾人雖有不滿,但看那女人疼痛難忍的樣子也就紛紛避讓在一旁。大漢把女人扶到桌前坐下,一邊用衣袖擦著臉上的汗一邊焦急地對五更說:“師傅,你快救救我媳婦吧,好好的腰,怎麼說痛就痛得受不了呢?八成是斷了,你一定要幫我救救她,我家裡還有個吃奶的孩子靠她奶大呢!”
五更聽大漢一說,摸著桌邊來到女人的背後,叫女人站了起來。五更伸手緩緩地摸了摸女人的腰,突然他扯住女人的褲腰往下一拉,頓時露出女人腰間三寸多寬的白肉來,女人殺豬也似一聲尖叫,一手提著褲腰一手掩著臉,起身就往寺外跑去。在眾人的哈哈大笑聲中,大漢先是一楞,接著拔腿就往外追趕媳婦去了。就在五更準備繼續給人看病的時侯,大漢手舉一根碗口粗的木棍大步走了進來,口中大聲罵道:“你這禿驢,竟敢在眾目睽睽之下調戲我媳婦,看我不打爛你這禿瓢!”五更緩緩站了起來念了聲阿彌陀佛!對大漢說:“施主請不要動怒,貧僧問你,你帶你媳婦是來幹什麼的?”大漢說:“來治腰痛的呀!”五更說:“那不就對了。你再看看你媳婦的腰好了沒有?”大漢一扭頭,只見自己的媳婦正雙手緊緊地抱著他舉起的木棍,低著頭朝他埋怨說:“你還不向五更師傅賠禮!你看,我這腰一點都不痛了!”大漢不信,硬是叫媳婦當著眾人試給他看,媳婦羞得滿臉通紅,照著丈夫說的左扭扭右擺擺,與來時判若兩人,她嬌嗔地對丈夫說:“你看這不是眨眼的工夫全好了嗎?一點都不痛呢!”大漢丟下手中的木棍,雙膝一跪,朝著五更叩起了響頭。逗得殿內拜佛的,燒香還願的,看病的眾人又一陣開心的哈哈大笑。
謝知府和同來的一行人也看得樂了,跟著眾人一通開懷大笑後。謝知府上前一步走到桌子對面坐了下來,看著五更問:“敢問師傅,你是如何得知這婦人的腰傷能用此法治好的呢?”五更若有所思,沉呤片刻,站起身來朝謝知府一低頭念了一聲阿彌陀佛說:“多謝施主屈尊光臨雞鳴小寺,貧僧這方有禮了!其實這婦人腰傷只不過是難者不會而已。聽她丈夫所言,貧僧已經知道婦人這傷是新傷而非陳年舊傷。貧僧一摸婦人腰間,見其骨胳健壯,同時摸到婦人身著粗布衣衫,因而貧僧斷定婦人乃是勞作之人,斷不會患淫逸之傷,必是突然扭傷所至,其實她自己只要多彎腰活動就可痊癒。可婦人大都耐不住疼痛,貧僧只好出此不雅之下策了。阿彌陀佛!”
五更一席話說得滿殿的人個個點頭,人人稱妙。謝知府既不點頭也不稱妙,繼櫝問道:“和尚本應拜佛誦經,師傅為何不去誦經卻給人治病呢?”五更答道:“我佛慈悲,普渡眾生脫離苦海,人生有八苦,肉生占其四,尤其以病為最苦,貧僧只不過是積小善為大善,積小德為大德,助人脫離病痛之苦不就是最起碼的普渡眾生麼?”謝知府又問五更:“那師傅看我有何病症?”五更又沉呤片刻緩緩答道:“施主暫無大礙。”“那何時有礙呢?”“三年以後。”“有何礙?”“白!”“何為白?”謝知府緊追著問五更,五更依然是緩緩而言:“此乃天機不可明言,施主只須牢記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定保無事!”
聽了五更的話,謝知府心中一驚,三年之後有無大礙他可以不信,在他眼裡和尚、道士大多故弄懸殊,真正道行高深者、立地成佛者能有幾人?可他就不明白,自己一行人自進這寺門並未露出什麼破綻,可五更一個瞎眼之人,怎麼就知道自己是個做官的呢?謝知府還在滿腹狐疑,五更又說話了:“大人是不是正在想貧僧是怎麼識破大人身份的事呀?
這個其實不難,無須大人這樣絕頂聰明的人去費心力。大人的心力須用在治下百姓身上才是。好了,你我今日已有一面之緣了,大人請回吧,貧僧還要為眾人解除病痛之苦呢!煩請大人記住貧僧今日所言,不然大人恐有性命之憂!”
打雞犬不寧鳴寺回來後,謝進才還時不時想起五更說的話,為官還算是清正廉明,四方百姓也能安居樂業。可太平日子一久,知府覺得做地方官也不過如此,這身體也沒見起什麼變化,神僧說的也不見得就准。漸漸地謝進才把五更說過的話扔到了一邊,再也不去想它了。
謝進才這一放鬆不打緊,骨子裡原本就有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貪婪之心就不知不覺地膨脹了起來。先小貪,後大貪,先是自己貪,後是手下各級官吏一齊貪。把一個原本清平安樂的治下攪得烏煙瘴氣,民不聊生,百姓個個苦不堪言。
說來也怪,這謝進才貪的銀子越多,他的肚子也慢慢地變得越來越大,開始還不覺得是個累贅,還真的以為是屬下拍馬所說的那樣——發福,誰知三年後肚子竟如小禾桶一般,別說是行走,就是到前衙審案也要四個大漢把他抬到文案後的太師椅上去,而且還不時隱隱作痛。謝進才遍請名醫診治,卻不見有絲毫消退。反而一日比一日大。這天謝進才終於倒在後衙的地上,肚子內有如刀絞火燎一般, 痛得他殺豬一般嚎叫。請來的名醫聖手個個看了只是搖頭,悄悄地叫他的家人準備後事。
正當眾人束手無策的時侯,當年陪同謝進才私訪雞鳴寺的縣令想起了五更說的“三年以後”的話,也記起五更當年曾說的一個“白”字,難道這個“白”是指白花花的銀子?難道知府大人的怪病是由貪銀而引起的?想到這裡縣令倒吸了一口冷氣,嚇得出了一身的冷汗,不由得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肚皮,此時他才後悔這幾年跟著謝知府也變成了一個千夫所指的貪官。
縣令把自己的想法對知府一說,謝進才也如夢初醒,縣令立即叫人紮了一乘軟轎,挑了幾名身高體壯的兵丁,抬著已經無力嚎叫仍在痛苦呻吟的知府大人,火急火燎地趕到了雞鳴寺。縣令拉著五更的衣袖也顧不得臉面和身份,不住地哀求著說:“五更師傅,五更活菩薩,你快出手救救知府大人的命吧,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哇!”
五更來到擺放在地上的謝進才身邊,彎下腰用手按了按他的肚皮說:“阿彌陀佛,施主可曾記得貪僧三年前說過的話麼?”知府用那雙死魚般的眼睛看著五更,無力地點了點頭。五更伸直了腰,像是對知府也像是對眾人,更像是發自內心的感悟,他緩緩地說道“我為僧者,是秉承佛祖旨意,慈悲為懷,普渡眾生,你為官者,秉承聖意應清正廉明,懲惡揚善。二者雖途不同則歸一至。佛與凡人並不遙遠,僅一字之遙。”覺“者成佛,”迷“者為人。但願”迷“者早日知返。阿彌陀佛!”
五更的一番話只聽得知府一班人如雞吸米般地點頭,這是他們第一次聽說佛與人的區別,第一次感受到心靈是如此的震憾。縣令還是忘不了他那躺在地上的上司,又拉住五更的袖子搖了搖說:“大師,請你快點動手吧,不然就來不及了呀!”五更大聲叫了聲:“玉兒,取針來。”隨即又對縣令說:“還是把這位施主抬到寺外的蔭涼處吧,不要汙了佛門清靜之地。”
一行人七手八腳地將知府抬到寺門外的大樹下,人們也都跟著像看耍猴一樣把知府圍在了圓圈中間。五更叫眾人往後退開幾步,彎下腰,接過小玉遞過來的一根二尺來長的竹針,照著知府的肚臍眼紮了下去。知府大叫一聲:“哎喲,痛煞我也!”兩眼一翻,竟昏死了過去。五更用右手的兩個指頭不停地撚動著手中的竹針,片刻工夫,竹針只剩下寸許露在知府的肚臍眼上,就像是一根剛燒完的香枝。眾人看得大氣都不敢出,四周一片寂靜。
就在這時,知府肚臍上的竹針自己擺動了起來。五更伸手捏住那擺動的竹針,大喝一聲:“出來吧!”右手一揚,將竹針拔了出來。竹針一撥,知府的肚臍眼“撲”的一聲,噴出一道黃黃的噴泉,一股刺鼻的醒臭味刹時彌漫開來。眾人不由得捂住鼻子朝後退讓。
這臭水一出,知府的肚子自然也就癟了。只見知府睜開雙眼,長長地出了一口氣,他雙手一按地坐了起來,環顧四周問:“我可是到了陰間?”縣令趕緊忙上前一把扶住知府,在他耳邊說:“恭喜大人,賀喜大人,五更師傅把你從陰間又救回了陽世,你的肚子已經消了。”知府這才想起自己的肚子,用手一摸,什麼話也不說翻身就跪在地上朝五更叩起了響頭。
就在這時,只聽眾人“哇”的一聲驚叫,知府肚子裡噴出來灑落在青石板上的臭水,竟在那青石板上形成了一個個白色的元寶圖案。五更叫人拿來鋤頭撬起這塊有元寶的青石,念了一聲阿彌陀佛!對知府說道:“佛祖葆佑,施主已無大礙了,這塊石板施主就請拿回去做個紀念吧!”
一行人又抬著知府走了,真的是把那塊青石板也抬走了。不久這塊有著“元寶”的青石出現在知府衙門的壁照下,背面多了兩個血也似的鮮紅大字“戒貪”。據說,打這以後歷任的知府再也沒有出一個貪官。士、農、工、商又各執其事,庶民百姓又能安居樂業!這是後話。
謝知府和一班貪官經此一折騰後,個個膽顫心驚,紛紛吐出了所貪的不義之財。眾官決定將這筆銀兩全部捐給雞鳴寺,可等他們一行人來到雞鳴寺時,寺中只有小玉一人,小玉說師傅已下山雲遊一個多月了,何時回來不得而知。五更去了哪裡,誰也不知道。